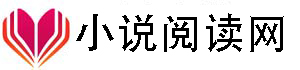150-160(5/26)
,习玉玲,戏子不就这样起名儿么。然而他叫席玉麟。他的师父很爱他,起了个尊贵的名字。世上很多人可以只知道对方的名字就共度一生,她和席玉麟什么都有过了,却不能读出他的姓名。
接下来的几天里霍眉什么工作都进行不下去了,一直在想自己该穿什么衣服,漂亮不漂亮还是次要,主要是得贵。挑来挑去,还是挑了那条钴蓝色缎面电光裙,外搭黑色貂裘。项链就不戴那条澳白了,贵是贵,但显得像何炳翀这么多年没给她买新的一样换条蓝钻吧,也将近十万了,且不如澳白那么浮夸,更典雅。
头发会不会显得少?
当天,她重新去烫了头,烫得又多又蓬松,还额外垫了假发片。距离开戏还有三个小时,就先回了趟厂里,叫上一个阿坤的伙计,“东西准备好没有?去叫马车吧,先搬到马车上去。”
阿坤忙应了一声,一会儿,他在外面叫:“霍老板,好了!”
霍眉对着镜子又整理了一下行头,最后戴上一顶带面纱的黑圆帽,才随他登上马车,往皇后戏院而去。她是第一个到的,所以坐在了第一排;感觉太近了,看不清脸,又往后挪了几排,最终定在了第五排的过道旁。
一屁股坐下,就再站不起来了。
陆陆续续有其他观众入场,孩子们窜来窜去,大人们高声交谈,她始终定定地坐在那里,人们的交谈声穿过耳朵,却并不留痕迹。后台已经做好准备工作了,右挂一个“出相”,左挂一个“入相”,中央悬“蜀戏冠天下”牌匾——她过去老见到这块牌匾,却不能认字,今天就一遍遍地读,要把过去的全补上,有一次是一次。蜀戏冠天下。蜀戏冠天下。
阿坤静悄悄地进来,坐在老板边上。
晚上六点,灯准时熄了,只剩戏台在发光。报幕员穿着中山装,笑盈盈地出来向大家招手,在介绍什么;霍眉统统听不进去。人一站在台上,她就死盯着对方的脸研究:是不是他?
不是他。
忽地锣鼓齐响,干冰造出的雾气漫了满台;等雾气退去,七个穿着彩衣裳的仙女就翩然从门后钻出来。她把屁股往前挪了挪,心脏在胸腔里跳得比锣鼓还快,叫她很难受。这七个仙女又乱动、又摇头晃脑,上着彩妆,根本看不清楚人脸。听声腔更不可能,市院和漱金的差别太大了,一开口,个顶个的嗓子好,没有谁的特别突出、特别熟悉。
又是一阵锣鼓响,七仙女下去了!
她轻轻地“哎”了一声,简直坐立难安,又把屁股往后挪、靠回椅背上,双手报臂,重重地呼出鼻息。
又有几个妖怪上场,和玉皇说着什么。席玉麟会不会又唱回生角了呢?也不是没有可能。她感觉很着急:什么破戏,这么多人在台上晃悠,叫人怎么认?虽说如此,还是尽力辨认着。生角的妆不浓,还能看得出大致脸型,没有属于席玉麟的那张小尖脸。
她正聚精会神地逐一打量,忽然又是锣鼓打响、吓了她一大跳。第一折子结束!
第二折的演员匆匆跑上台来,几个须生,其中万万不会有席玉麟。她不看他们,只闭上眼,反复回忆刚才那几人的体态、腔调,觉得这个也有点像,那个也有点像,却没有哪个特别像。待七仙女又跑出来,她的屁股也再次滑到座椅前端,眯起眼睛逐一打量。
一个可怕的想法萌发出来:我兴许不认得他了。
分别的时候,席玉麟才多大?他的模样还没定型,再者,红气养人,苦难摧折人,不知道他受过哪一种,但总之不会和分别的时候一模一样。譬如霍眉自己,变化多大呀。
想到这里时,七仙女开始转着圈儿舞水袖,转得飞快,那水袖也像个柔软的圈